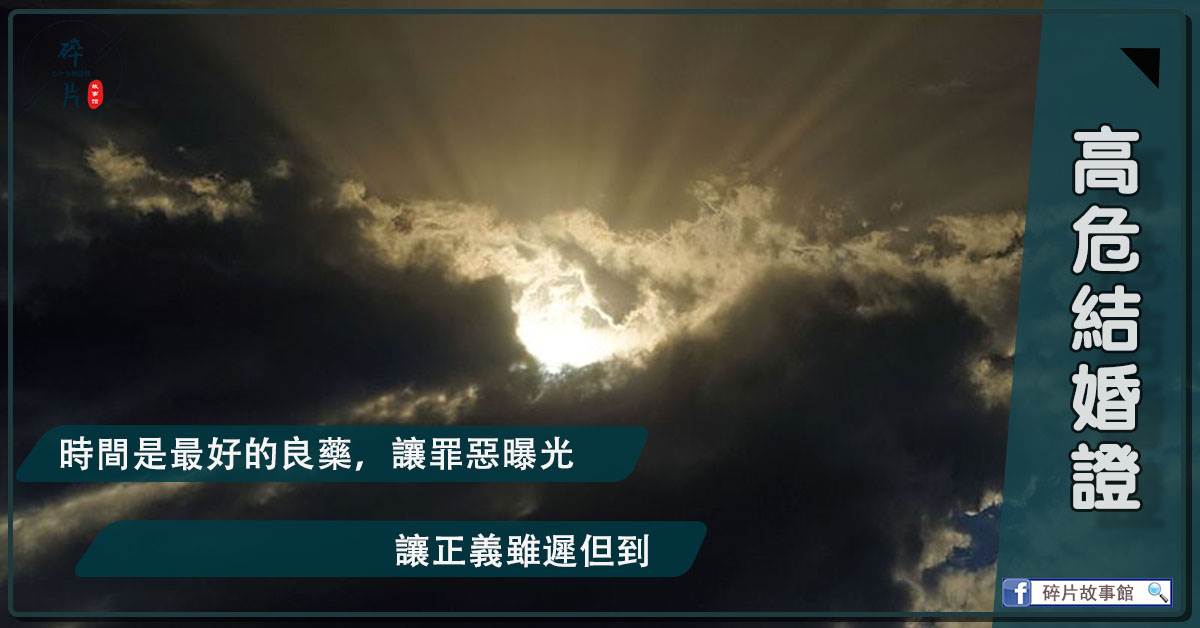《高危結婚證》第4章
我繼父亡了,這房子若要分,那得是分我繼父的那部分,再一分為二,按市值最多也只能給任高飛四分之一,也就是八十多萬。
可是他不滿意,說什麼那房子是他爸爸的,自己至少要一半。
就這樣,前兩年為這房子的事,我們兩家也沒少扯皮。
后來我和我媽不堪其擾,干脆把房子給賣了。
錢多錢少讓法院去判,最后的結果當然沒什麼懸念,年初那會兒就判下來了,錢也跟他家結算清楚了。
我就是怕他總來騷擾我媽,才讓我媽回老家的。可是這人要是不講道理,那可比癩皮狗還要賴皮。
我回到單位,看到任高飛坐在我的椅子上,雙腿翹得高高的。
已經臨近下班,辦公室里外都圍了不少人。
我上去一把就把任高飛的煙給扇飛了,我說你想干嘛?
「我想干嘛?任小琪,你不把我該得的那份吐出來,今天你就別想囫圇離開這兒了!」
我說行啊任高飛,幾天不見,能耐見長啊?
你跟我要多少,我就給多少,那法院是幼兒園啊?
「你有種在這兒立霸,你有種繼續砸啊!我們有保安,有警察,我還怕你鬧不大呢!有種你往我這兒招呼——」
我指著自己的腦殼,笑他是個孬種:「今天你要是能把我放躺下了,回頭坐個十年八年的牢,我反倒清凈。」
見我壓根不吃硬的,任高飛又軟了。
「小琪,咱們怎麼說也是兄妹一場嘛,你也不能眼看著你哥走投無路是不是?我最近做生意虧了點,你說你和姨兩個人手里握著好幾百萬呢,也沒啥急用場是不是?先借我點唄,回頭我賺了,我給你們分紅——」
ADVERTISEMENT
「滾。」
我輕蔑地看了他一眼,一個字都不想多說。
我的態度激怒了任高飛,他一蹦三尺高,指著我的鼻子辱罵我:「任小琪你以為自己是個什麼東西,你跟你媽兩個嫁進來,不就是賣*的爛貨麼?我爸*完你媽再*你,你當我不知道是吧?」
「咣當」一聲,我操起手邊一個訂書器,直接砸在了任高飛的腦殼子上!
我在拘留所里待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,陸尋帶著律師進來,把我保了出去。
后來我才知道,他跟任高飛私了的,賠了他五萬達成了和解。
我連一句感謝都不想說,我一路跟在他身后,像他提在手里的行李箱。
快到家的時候,我說:「我上去收拾東西,明天咱倆去離婚。你把喬禾和小蛋接回來吧。」
陸尋哭笑不得:「小琪,你怎麼就一根筋呢?我和那孩子哪里長得像了?」
陸尋說,喬禾可不是他前妻,甚至一點關系都沒有。
她只是他的病人,一個有著嚴重心理障礙合并妄想抑郁癥的女病人。
單身未婚,卻帶著一個兒子。
陸尋說,自己只是看她太可憐了,偶爾多關照了一些。
結果,這姑娘妄想癥犯了,非要說他是她的男人。
聽完這些,我不厚道地笑了:「話說,女病人愛上自己的心理醫生本來就是很常見的事,否則怎麼叫病人呢!但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,你怎麼能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呢?還帶著人家母子兩個去迪士尼,你可真敬業啊!」
我犀利地提出了質疑,甚至已經做好了抨擊的大綱。
誰叫我是個以筆代槍的有良知的新聞人呢?
「瞅你這幸災樂禍的混賬樣!」
ADVERTISEMENT
陸尋瞪我。
我說,那可不,我是記者,致力于挖掘事實真相。
「行,你要想寫喬禾的事,以后我保證你有機會。」
陸尋這個烏鴉嘴,竟一語成讖。
臨近五點半的時候,喬禾的母親打了電話過來。
我和陸尋飯都沒吃,急忙出門。
喬禾站在醫院的天臺上,穿著一件素白色的長裙,隨風起舞。
「喬禾!」
我和陸尋跟著保安爬上樓頂,此時警察還沒到位。
「小禾,小禾!小禾你快下來啊!」
喬禾媽媽坐在一旁的水泥地上,哭得力竭聲嘶。
「喬禾!」陸尋大聲呼喊著:「你冷靜一點,想想小蛋,想想你媽媽!快回來,不要做傻事!」
喬禾回過頭,長發被風吹散,笑得甜美又凄絕。
「陸醫生,謝謝你。我已經想起來了很多事……給你添麻煩了,真抱歉……」
陸尋白著臉色,一邊大喊她的名字,一邊試著往前靠近。
「你別過來!」喬禾激動大叫。
陸尋不敢再動,「喬禾,聽話。既然你什麼都想起來了,你就應該明白,那些噩夢已經過去了。你聽話,下來。」
「不會過去的。」喬禾搖頭,「永遠不會過去的,我已經毀了,我的一輩子都毀了,還有我可憐的小蛋,只要我活著,他就永遠會被別人指指點點。除了死,我沒有別的路可走了!」
「不!這不是你的錯!喬禾,你是個好姑娘,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應該為此付出代價。但這個人,絕對絕對不應該是你和小蛋!」
喬禾的淚水隨著風飄過來,落在我的臉頰上,燙出我心口上的共情。
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喬禾身上發生過什麼事,只是一低頭,我看得到我手腕上陳年的傷——
我想,那種共情,大概來源于這個世界對女孩子們的敵意。
「陸醫生,謝謝你。」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